最近读了17世纪的汉萨同盟、16世纪西班牙帝国征服印加帝国等欧洲殖民帝国的故事,我深深感受到跟当前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相似之处。
帝国中央提供授权和支持,让探险家、商人等用户去开拓盈利,然后从中抽成获利。这种模式与现代互联网平台在网络效应和利益分配上有相似之处。我核心要讲的是15世纪至20世纪早期几个主要殖民帝国的历史案例,包括西班牙帝国、荷兰与英国的崛起、汉萨同盟的盛衰,以及大英帝国在近代的兴盛与瓦解。
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将相历史,是金字塔结构的顶峰,与平台经济还是有差别;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尽管跌宕起伏了40年,但是可参考的商业底蕴还是太少;互联网平台最早就是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的发明,传承了殖民体制的衣钵和knowhow,所以当今的互联网平台,与其说从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史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史中吸取养分,还可以再看看欧洲殖民史。
从史实出发,我们分析这些平台式帝国的权力与收益结构如何推动其兴起、更替,并尝试提炼对当代互联网平台生态的启示。
(一)西班牙帝国的平台征服模式
15世纪末到16世纪,西班牙率先在美洲建立殖民帝国。与其说西班牙探险家寻找无人荒地开垦,不如说他们更钟情于已有富庶社会但技术相对落后的地区,以实现以少数征服多数的统治。这跟开疆扩土的扩张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一个典型例子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对印加帝国的征服:1532年,皮萨罗仅率约180名士兵即俘虏了拥有数万军队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这种以寡制众是利用了当地社会的高度组织的机会。西班牙人擒贼擒王,夺取最高权力,利用原有官僚体系和土著劳力为己服务。
西班牙王室为激励征服,设计了一套类似现代平台的授权机制。探险征服采用契约制:探险者自筹资金远航,王室授权其以国王名义占领治理新领土,并订立收益分成。以皮萨罗为例,1529年西班牙与他签署《托莱多契约》,授予其在秘鲁地区探索征服的总督头衔。条款规定:皮萨罗承担全部征服费用,王室不出资;作为回报,皮萨罗就任总督,每年领取72.5万马拉维迪年薪(约合当今24万美元),但此薪资从未来上缴王室的殖民收益中扣除。
换言之,王室拿走殖民地未来财富的“大头”,探险者只获得固定收益和头衔。这类似平台与内容创作者的关系:平台提供机会和名分,给创作者勉强保本的保底,让创作者去“跑马圈地”。大部分创作者只能拿到保底,小部分创作者作出爆款,获得高额收益优先返还平台方。除了固定收益,征服成果也按约定分配:一般而言,王室抽取白银黄金的20%(即王室五分之一税),其余按出资和军阶分配。参与远征者多为逐利的机会主义军人而非受饷正规军,他们自带马匹武器参战(跟现在的创作工作室类似),胜利后按贡献分得战利品。远征者虽然拿80%,但是承担了统治、治理当地的义务,最后很可能把人都搭进去。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后,最后的结局是,在傀儡印加国王曼科的起义和西班牙殖民者阿尔马格罗的反叛下被杀死。阿尔马格罗在杀死皮萨罗后不久,又被新的反叛者杀死。这一机制有效降低了王室风险成本,让众多冒险者前赴后继开疆拓土。
在这样的平台框架下,西班牙帝国以极小投入换取巨额回报:大量黄金白银源源不断从美洲流向欧洲。新大陆的征服带来海量的金银:据估算,1500–1600年间从美洲运抵西班牙的白银超过18,000吨,占当时欧洲流通量的80%以上。“日不落帝国”称号最早就指西班牙。在这个阶段,西班牙的平台战略特点是中央集权+特许合同:王室高高在上掌控资源分配,通过契约让冒险家替其打江山,将美洲高度组织的阿兹特克、印加等帝国纳入版图。
(二)日不落帝国易主——英国崛起与西班牙衰落
17世纪后,西班牙的全球霸权被英国逐渐取代。造成这种更替的不仅是国力消长,还有两种殖民“平台”模式的差异。西班牙帝国由官僚体系直接管理殖民地,贸易上实行重金主义封闭政策(殖民地只能与宗主国贸易);而英国则更依赖私营公司和市场机制,在海外扩张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效率。
从商业模式看,西班牙通过塞维利亚的“印第安贸易之家”垄断殖民贸易,重税垒高壁垒;反观英国,更愿授权私营特许公司开拓。例如,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便获皇家特许垄断英格兰对印度和东方贸易。与西班牙由王室委派总督治理殖民地不同,英国在亚洲主要依托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商业实体。正如史家所言:“征服印度的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一家私营公司”。1693年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颁发给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就规定了公司的经营特权和规章,可见王室授予其高度自主权。结果,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坐拥连年暴利,自备雇佣军超过英国本土军队规模,一度实际统治了整个印度次大陆。这种“公司治国”模式下,英国王室和贵族亦间接获利:许多英国贵族持有公司股份,共享殖民红利。
英国取代西班牙的过程,也体现了新平台对旧平台的革新。英国利用更合理的激励机制(如允许移民在北美拥有土地自治、通过公司让更多人分享投资回报)来吸引人力资本,从而迅速扩张版图。例如,在北美十三殖民地,英国最初通过维吉尼亚公司等募集移民建立殖民点,之后虽改为皇家殖民地但仍允许一定程度自治,这与西班牙严格官控形成对比。更分散的利益分配让英国殖民体系更具活力。
英国这种更灵活开放的制度,只是让英国具备了可以跟西班牙掰手腕的能力。西班牙的衰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黄金。
黄金是西班牙平台兴起的原因,恰恰也是它被取代的原因。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因为王室靠向外掠夺、抽成这种方式太过成功,最终都转化成黄金送到西班牙王室,带来了几个坏处。一是,巨额财富掩盖了体制低效和官僚腐败,使得经济利益越发金字塔化、结构固化。二是,靠掠夺致富不管生产,国内工商业萎缩,产业空心化;三是,黄金激增导致物价飞涨,即使挣到一些收入也只是勉强生活,人们对西班牙王室意见很大可是无奈西班牙王室又掌握最多的钱做分配。四是,西班牙王室当时认为黄金和白银是源源不绝的,因此一直在打仗,跟法兰西打、跟荷兰打,跟奥斯曼打,跟普鲁士打……所有人都在孕育对西班牙的不满。
英国无法仅仅靠自己的“制度优势”就战胜西班牙,他还要等待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西班牙吸黄金这个毒要够深,让人认为黄金无所不能,只要挥舞黄金这个武器,大家都会继续聚拢到西班牙这个平台下。短期内大家是打不过就加入,但是长期看世界上人们的不满和怨气是在积累的,再加上产业空心化。而英国去中心化、竞争式的体系逐渐造出更好的船、培养出更厉害的海军,在1588年英国击败“无敌舰队”,重创西班牙海权。
而且英国取代西班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反复的。从1588年“无敌舰队”战败算起,到英国真正全面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霸主,还经历了60-80年的过程,这个过程穿插了荷兰的崛起,虽然说荷兰最后还是被英国盖过去。
(三)荷兰海上帝国与英荷竞争
17世纪的荷兰崛起,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平台”。荷兰的帝国实力来源于具有鲜明的商人本色:由公司和城市主导,而非王室直接管理。汉萨同盟时期,荷兰曾受益于北欧贸易联盟的网络(例如汉萨的航线和市场为荷兰城市提供了商机),但随着荷兰自身实力增长,他们也从汉萨手中夺取贸易主导权。
汉萨同盟(Hanse)是一个不同于殖民帝国的“平台”——它是由一系列北德意志和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组成的松散商业联盟。自13世纪起,汉萨城市为促进远程贸易、护送商队和抵御盗匪而联合,形成了跨国的商贸网络。汉萨同盟给予成员城市的商人许多特权:比如在他国港口的税费减免和司法自治权;在伦敦、布鲁日、诺夫哥罗德、卑尔根等地设立驻外商站,享有治外法权。可以说,汉萨同盟提供了一个共享的平台,各城市商人通过联盟网络进行合作和垄断,在14-15世纪一度主导了北欧的海上贸易。

1400年汉萨同盟扩张范围图。松散的汉萨城市联盟在15世纪达到极盛,覆盖了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大部分重要港口。。
从制度上说,汉萨同盟和荷兰帝国,跟英国一样,都是去中心化的商人主导的帝国。但是荷兰最终为何又败给英国呢?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海上商路的效率远远高于陆地商路的效率。从地图可以看到汉萨同盟基本上是沿着欧洲北部的一条陆地商路。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运送毛皮木材、到瑞典贩卖鳕鱼、到汉堡的谷物啤酒、到荷兰安特卫普的葡萄酒和盐和奢侈品,是中世纪最早的欧洲多边贸易平台。
但是英国的贸易线路,是跨大洋的贸易网络,超越欧洲的市场,真正的全球化供应链平台。跨大西洋三角循环:第一边(欧洲 → 非洲):英国船只从伦敦、布里斯托等港口出发,装载纺织品、火枪、酒、金属制品等工业品。第二边(非洲 → 美洲):在非洲贩卖工业品换取奴隶。第三边(美洲 → 欧洲):奴隶被送往加勒比与美洲种植园劳动,产出的糖、烟草、棉花等原料再运回英国。英国船只空舱率几乎为零。还有东方殖民地循环:印度与东南亚的棉花胡椒茶叶靛蓝等初级农产品,英国用纺织机做成的工业制品,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跨大西洋三角和东方殖民地循环,都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才变得可能。
海上贸易压倒性优于陆路贸易,这是一个地理常识。同等距离下,海运成本仅为陆运的1/20,而且运量是陆运的100倍。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典型“大印度帆船”为例,可以载重1500吨,只需要配备几十名船员,风帆动力靠大自然,运输成本就是船员的吃穿用度;而陆运每增加1吨,都要线性增加车辆、畜力与车夫。1500吨,需要1500辆牛车,配备1000个车夫,而且沿途翻山越岭,还有磨损损耗,沿途还要住驿站,各种买路钱。
第二个原因,荷兰和汉萨同盟,去中心化去得太过头,太松散了。
汉萨的结构先天松散,没有中央政府、常备军和统一财政。汉萨商人在伦敦的基地——“蒸汽磨坊(钢厂,Steelyard)”曾长期享受免税贸易特权,引起英国本土商人的不满。16世纪中叶,英国政府开始打压汉萨特权:1551年爱德华六世取消了汉萨在伦敦的免税权;汉萨成员之一的汉堡甚至私下与英国议和以保自身利益。1597年,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下令彻底驱逐汉萨商人,查封伦敦钢厂,宣告汉萨在英格兰经营的终结。
后来继承了汉萨同盟遗产的荷兰共和国(即尼德兰联省),在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正式的股份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由政府授予垄断远东贸易权,向公众募股集资,其股份可自由转让,在欧洲资本市场开创了股票交易的先河。这一创新的商业平台汇集了当时巨额资本,用于建立全球贸易网络和殖民据点。这个制度跟英国很类似,因此英国和荷兰都压过西班牙,开始争夺新的霸权。但是,英国在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现在英国央行的前身),成为英荷争霸的关键性要素。英国政府以发行公债的方式筹资,英格兰银行则以储户资金认购公债,从而获得利息回报,英国政府获得了稳定、可持续的长期借贷能力,支撑其进行长期战争投资。《货币战争》中罗斯柴尔德的发家史,就是罗斯柴尔德利用信息差,在滑铁卢战役英军战胜后几个小时内,利用市场心理操控伦敦公债价格,低位吸纳、随后暴涨,在几天之内成为欧洲最富有的金融势力。那个时候,英国公债已经是英国国家信用的证券化产物。而荷兰虽早期领先,但国家资源有限且缺乏统一指挥(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公司,战时需与国家政策协调,存在掣肘)。最终,英国利用更强大的国家—公司结合(皇家海军+东印度公司)取胜。
融资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 就成为新竞争者的决胜因素。
(四)大英帝国的巅峰与殖民体系的瓦解
经过18-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和海外争霸,英国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荷兰等),建立起维多利亚时代空前庞大的大英帝国。到1920年代,英国统治的领土面积达3,55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球陆地四分之一,人口超过4.49亿,被誉为“日不落帝国”。这个横跨欧亚非美的大帝国其实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先是以北美和印度为核心的18-19世纪殖民扩张;继而是19世纪末至一战后的非洲、中东扩张和全球霸权。然而,20世纪上半叶又见证了其快速解体。分析这一盛极而衰的过程,可以看到平台机制在不同时空下的演进与崩解。
19世纪的大英帝国依然沿袭平台化治理的特点:间接统治、利益捆绑。在印度,英国在1858年废除东印度公司统治、改由王室直接管辖后,仍维持大量土邦王公的世袭统治地位,采用“藩属联盟”方式统治广土众民。少数英国官员通过印度土著官僚体系和亲英精英阶层,实现对数亿人口的有效控制。这类似于现代平台依托众多本地合作伙伴扩张规模:英国平台让印度本地统治者、商人分享一部分权力或利益,从而降低直接管治成本。同时,帝国在经济上深度绑定殖民地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形成全球化的分工网络。这种网络效应加强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例如英国工业品倾销印度,印度棉花、茶叶、鸦片则源源运回英国,殖民地被纳入大英帝国经济圈。
然而,到20世纪早期,此平台的弊端逐渐显现并走向瓦解。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重创宗主国实力,英国无力再维系庞大殖民体系;另一方面,殖民地民族主义高涨,要求自决独立的呼声愈演愈烈。殖民平台的收益分配日益失衡:大部分利润流向宗主国,本地精英和民众获益有限,甚至饱受剥削(如印度在英国治下人均收入停滞不前)。这种情况下,“用户”纷纷退出平台——殖民地要求独立。1920年代起,英国被迫以自治领形式给予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白人殖民地高度自治。二战后更是殖民独立的高潮:1947年英属印度分裂为印度、巴基斯坦两个独立国家,随后十余年间亚洲、非洲殖民地密集脱离英国统治。不到二十年,大英帝国土崩瓦解:其直辖殖民地从1945年的逾7千万人口迅速降至1970年的不足500万。历史在这一刻转折——延续数世纪的殖民帝国平台全面崩盘,取而代之的是独立民族国家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帝国平台的终局并不相同:西班牙帝国因自身衰弱和殖民地反抗在19世纪崩溃(1898年美西战争失去最后的古巴、菲律宾等殖民地);荷兰法国等帝国也在20世纪中叶相继瓦解。而大英帝国作为最后的典型,在瓦解时倒是体现了一定“平稳转型”——部分殖民地加入英联邦,与宗主国保持象征性联系。但无论过程如何,传统殖民平台在20世纪已整体退出历史舞台。正如英国首相麦美伦在风起云涌的非洲独立运动前感叹的那样:“变革之风正在吹遍非洲”。旧平台已不能满足“用户”(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诉求,不得不退出。
下一个帝国,是美国。但大英帝国不是被美国打败的,是他自己跟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扯裂的。美国的故事,就不是殖民平台的故事了。
(五)平台兴替的规律
回顾上述几个世纪的殖民帝国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平台兴起和更替的共同逻辑。
首先,成功的平台善于调动外部力量。西班牙王室通过契约吸引冒险者,英国授予公司和移民特权,都是用利益机制吸引众多参与者为己所用。就像当今互联网平台让第三方开发者、内容生产者加入生态以实现规模扩张一样,殖民帝国的平台模式极大扩张了宗主国的触角。例如,西班牙凭借区区数百征服者就降服数百万新大陆土著,这背后是其提供了征服许可和财富分成的诱因,使大批亡命之徒前赴后继。这种网络效应在历史上同样明显:参与者越多,征服越顺利,帝国版图越扩大,又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平台的利益分配与治理结构决定其寿命。如果平台过度垄断利益、剥削参与者,往往会引发反抗或被竞争者挖角。西班牙对殖民地财富的高度垄断(例如实行殖民贸易垄断、沉重税赋)导致殖民地精英和商人心生不满,给他国提供了干涉或夺取的机会。相形之下,英国在早期给予北美殖民者一定自治和土地产权,因而殖民地发展迅速(尽管最终仍因利益冲突爆发革命)。同理,现代平台若一味汲取用户价值、不予回馈,用户和合作方就可能倒向别处。平台更替的一个模式是:新平台通过更优厚的收益分配或创新模式吸引原平台的参与者,从而实现用户和资源的迁移。17世纪荷兰、英国正是用更市场化的方式(高额分红的公司股份、开放的航运贸易)吸引了欧洲的资本与人才,战胜了刻板守成的西班牙官僚体系。
第三,技术和环境的变迁往往催生新平台。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技术开创了全球贸易航路,使中世纪的汉萨的陆路贸易网络迅速过时。工业革命又赋予英国等新手段(蒸汽船、铁路、电报)来统治远方,比起依赖帆船和徒步的老帝国具备压倒性优势。同样地,在互联网领域,每次技术革新(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AI等)都诞生新的领导者,取代老巨头。
最后,治理的灵活性与包容性至关重要。汉萨同盟没有中央权威,成员各怀算盘,在应对外敌时屡现离心;反观英国在竞争中善于调整策略,例如在不同殖民地采取差异化统治(直接管理或间接统治并用),这提高了平台的适应力。同理,现代平台需要平衡各方利益、灵活应变,才能防止“用户出走”或政策环境骤变带来的崩盘。殖民帝国时代的更替提醒我们:当新的平台模式更能契合时代需求时,旧的平台即使曾经强大,也会加速衰亡。英国首相霍拉肖·瓦尔坡早在1770年代就批评东印度公司的贪婪统治,警告其在印度引发的大饥荒和暴行。事实证明,公司治下的弊端最终促使英国政府收回特许,转型为直接统治。这类似今日一些平台在野蛮生长后受到监管介入、被迫整改以符合社会利益。
从15世纪的西班牙到20世纪的英国,全球霸主几经轮替,其背后是平台思想在起作用:通过制度和网络整合资源、扩大版图。然而,平台盛极而衰亦是常态。当内部矛盾积累或外部环境变迁,旧平台难逃被后来者超越的命运。对于当代互联网巨头而言,这些历史经验具有警示意义。
正如历史上所有日不落帝国最终都迎来了日落,当今任何看似稳固的垄断平台也终会面对后来者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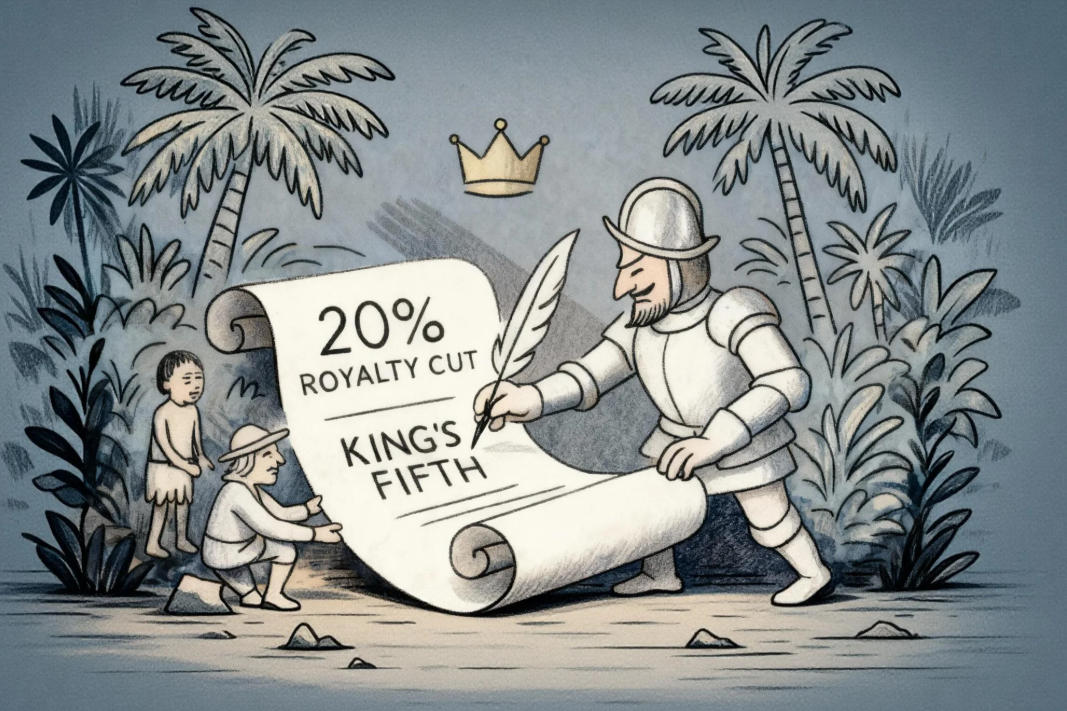
发表回复